杜周:酷吏传家财巨万
仅以好大喜劝、黩武嗜杀的特点而论,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竟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殊途同归。这与其说是汉武帝对儒家文化作了误读,不如说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对汉武帝进行了精心的误导。为了“与时俱进”,他们取汉初黄老学术成果,杂“天人感应”之说,对先秦儒家文化进行“包装”,推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系列“新儒学”产品,以迎合当时政治需要。汉武帝欣然将这些东西拿来树立君威,构筑“大一统”文化藩篱,却独将儒家文化最核心的“仁政”主张抛到九宵云外。《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西汉十位酷吏,有九位出自武帝一朝,说明在这样的独夫强权时代,酷吏必然成为急用人才,被大量发现培养使用。十大酷吏最后一位的杜周不仅以为政苛酷、治狱残暴位列三公,他的两个儿子做上高官后更加“发扬光大”,“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真是君有臣效,父有子继!
传载:“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南阳位于今河南与湖北交界处,著名酷吏宁成亦出此地;而杜周追随的这位主子义纵,则是继王温舒之后又一位出身黑道的酷吏豪俊:他早年横行乡里,与匪首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因他姐姐行医得幸于王太后而一夜发迹,弃盗从政,很快便以酷政声名远扬。杜周辅助这位外来主子首先立稳南阳地盘,然后敲山震虎,锋芒直指那位“过了气”的老酷吏宁成,“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最终以罪株连,不仅“成坐有罪”,而且当地孔氏、暴氏等豪门望族悉遭灭顶之灾,以至“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一地从官绅到平民都“重足一迹”,吓得不敢迈步向前。南阳被折腾得底朝天,杜周与其主子义纵扬威立万:义纵另有重用,杜周则升迁为廷尉史,被官声更酷的一代豪吏张汤收入为手下干将。
西汉的廷尉是主管全国狱讼最高官吏,杜周担任廷尉史,是廷尉手下要员之一。出身基层的杜周表现显然很让张汤满意。传载,张汤喜欢借请示案件之机向武帝夸耀下属,提到杜周,“数言其无害”。唐代颜师古注汉书,释“无害”为“无比”、“无人能胜之”,可见张汤对杜周满意度之高。不久,杜周被任命为御史,从司法系统进入了监察系统,还获得朝廷下派独立工作的钦差身份,手中握有督导并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
也许是张汤“无害”的评语给皇上印象太深,御史杜周被直接被派到汉武帝最重视的地区:边郡。武帝执政后连年征战,平南越、伐匈奴、征大宛,四面战火不断;而地处边防的郡县时有陷落,不断调往前线的边卒也大量逃亡。杜周深解皇上的忧虑,一俟上任,大开杀戒,使作战意志涣散的前线官兵只得纷纷调头向敌。那些守土不坚定的地方官吏中很多人被立案严办,也都从此不敢懈怠。杜周以钦差受命,得以向皇上直接奏事,其奏章多合上意,赢得武帝信任有加,旋即又被升为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相当于御史大夫的次官,掌有纠弹百官之权,其实也就是国家监察系统的常务副主管。司马迁特意提到杜周做这个中丞是“与减宣相编”,也就是说,这个职位上,是由他和减宣二人轮岗担任的。减宣是《史记·酷吏列传》里的又一人物,他在承办主父偃案件和治淮南王刘安反狱中,“微文深底,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受到汉武帝提拔。但减宣当了近二十年的御史和御史中丞,“数废数起”。而杜周在御史中丞任上也前后干了十几年,由此可推知,减宣几次被“废”时的接替者便正是杜周。就这样,两位酷吏在同一个岗位上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着。他们深知武帝对他们的“殷切期望”,那就是:在酷吏的道路上,没有最酷的,只有更酷的。减宣资历深于杜周,且手段老辣,缺点是过于苛责下属,事无巨细喜欢亲历亲为;杜周是后来者,比较好学,“其治与宣相放(仿)”,却又独具“重迟,外宽,内深次骨”的特点。两人就这样取长补短,比学赶帮超,多年之后皆成正果,被分别派到能独掌一面的更理想岗位:“宣为左内史”,执掌京师重地;“周为廷尉”,当上了最高司法官。一对酷兄酷弟皆大欢喜,他们执手相别,各赴重任。
哪知此一别竟成永诀。酷吏实是一条高风险的为官之路,十大酷吏大多不得善终。数年后,减宣在一次清理门户的追杀行动中,流矢射中上林苑大门而犯大逆,论罪当族,自杀了之,终于为他的御下过苛付出生命代价。而杜周则属于酷吏中的少数幸运儿,除为人圆滑,在廷尉任上,他高度效法老上级兼师长张汤的成功经验,办理重大案件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上所欲挤者”,他就顺势陷害;“上所欲释者”,便“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经过一阵这样的冷处理也就无罪开释了。杜周渎法阿上总是尽力做得巧妙无痕,但还是被明眼人看出了破绽,招来质问:“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汉代法律皆书于竹简之上,简高三尽,故以代指。对此,杜周则不慌不忙,从容应对:“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杜周的这套皇权高于法律的法理观和“以言代法”的执法准原则,其实正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法律的正统,就连无比崇尚法律的各派法家学说,也都不能摆脱这种君权至上思想的根本束缚。张汤与杜周先后担任廷尉,致使“诏狱”(以皇上旨意查办的政治案件)大量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尤其到后来,“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诏狱往往牵连广泛:“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诏狱大量使用刑讯逼供:“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有些诏狱因难以诬判而久拖不决:“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量的诏狱致使人人自危,出现了“闻有逮皆亡匿”的恐怖氛围。
杜周的酷吏生涯也曾陷入危机,却是逢凶化吉。传载:“周中废,后为执金吾”。虽改行负责禁卫,却依然表现出色。“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杜周真的如他在武帝面前表现的那么“无私”吗?我们还是看司马迁的春秋之笔:“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古以亿为“巨万”,虽身家数亿,杜周仍如开篇所述,将河南、河内二郡“夹河为守”的两位爱子培养成了下一代酷吏,大约是受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启发。至于那“渔”的方法,其实不必说得太穿——《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这位开国老帅当年身陷冤狱,受了酷吏凌辱,也不得不“以千金与狱吏”,并在事后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读此,便可略解杜周把为官“酷道”当做家传绝学的“价值判断”了。
- 上一篇:张汤:亵玩法律如儿戏
- 下一篇:霍光:治家不严致族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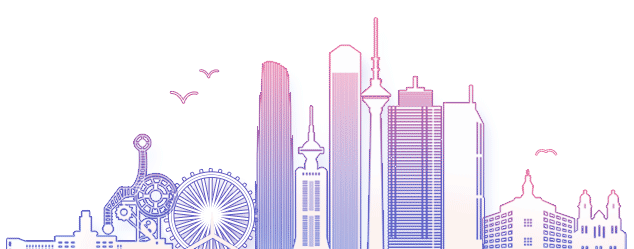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