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郑某,某省属国企A公司(国有独资)总经理,长期在国有企业任职。A公司为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启动并购该省某民营企业B公司的工作,并明确由郑某牵头开展。郑某考虑到刚到A公司任职不久,为尽快取得工作成绩,其在项目尚未完成尽调的情况下,授意公司战略部一周内完成可行性分析报告,且将本应提交党委会前置研究的重大事项,以时间紧迫为由直接提交总经理办公会,会上仅经简单讨论即由郑某拍板通过。由于尽调未实际完成,A公司没有及时发现B公司隐瞒巨额债务问题,且市场行情发生变化,该项目宣告失败,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审理意见
郑某作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明知尽调不充分、规避集体决策程序有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超越权限决策,造成国有公司资产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调查过程中,郑某以项目开展系由集体决策、市场因素不可预见、本人没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等理由提出申辩。我们认为郑某的申辩理由不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郑某行为系以集体决策形式掩盖个人专断实质。根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滥用职权,违反决策原则和程序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三重一大”事项。郑某的行为已经明显违反关于集体决策程序的规定,其为尽快取得工作成绩,在错误政绩观的驱使下,无视项目尽调尚未完成的事实,规避法定程序,将项目仓促提交总经理办公会集体研究,且在参会人员未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便拍板决定。整个过程看似经过集体决策,实则通过压缩会议讨论时间、减少无法由个人掌控的集体研究环节(党委会)等方式操纵最终决策结果,其实质应认定为个人违法行为。
二是郑某的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财产损失究竟是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或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的,还是不可抗力、难以预测的介入因素导致的,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对引发危害结果所起作用的大小,从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本案中,主要分析郑某的违规决策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对方隐瞒债务及市场行情等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等。郑某为推进项目未充分开展尽调,导致没能发现标的公司债务问题是造成重大损失的直接原因,市场行情变化因素是引发这一后果的诱因之一。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市场行情变化属于较为常见的介入因素,相关规定中对重大投资项目设计多次集体讨论决策程序的初衷就是为了最大限度控制风险,是郑某的刻意规避导致“防火墙”未能发挥作用,其行为具有导致最后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应当认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是本案中郑某主观上是故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往往会映射到客观行为上,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是滥用权力还是不负责任来判断其究竟系故意还是过失。根据相关规定,“严重不负责任”通常表现为工作中轻率大意,在重大经营决策时,不认真分析研究、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听取多方意见建议,盲目决策等;“滥用职权”则通常表现为行为人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处理无权事项或背离职务要求胡乱作为以及故意不履职等,其中违反规定、不顾法定程序,在重大经营决策方面独断专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郑某作为长期在国有企业任职的领导干部,明知“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的要求及其重要性,仍故意规避;在尽调不充分的情况下,独断专行通过投资决议,且其任职经历应当能让其清晰地认识到该行为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也未采取任何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而是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综上所述,郑某的主观上并非过失而是间接故意,其行为应认定为滥用职权。(周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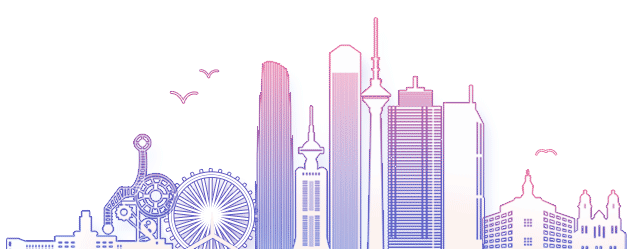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