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新者日进也。”山东曲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基点,焕发出无限生机。孔子研究院、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作为“新三孔”,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成为教育研究、文化体验、知识传播的综合性新型文化载体。图为曲阜市尼山圣境。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江西景德镇在传统瓷文化“原料”中加入时代化“配方”,文化自信的窑火在传承和创新中燃起新的生命,这里的“年轻范”和“国际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图为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一景。 新华社记者 卢哲 摄
嘉宾:
王学斌(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飞(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本报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进行解读。
1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是那种割断历史与传统的无根基创新,而是强调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创造
王学斌:《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极其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文明倡导创新、从不惧怕变革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中华文明于无数次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中一往无前、再造奇迹的确认与强调。
宋立林:中华文明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一概括,无疑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而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1987年,已经92岁的冯先生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旧邦新命,成为其格外关注的一个命题。确如冯先生所言,“旧邦新命”是中华文明得以“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显著特征。
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未曾中断,经历过难以缕数的灾难与挑战,但都能成功应对,继续发展,成为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古老文明,与其文明自身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是那种割断历史与传统的无根基创新,而是强调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创造。在旧与新之间,中华文明展现出明显的辩证性格,即“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儒家经典《大学》讲:“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周易》中的“鼎”“革”二卦,“损”“益”二卦,都充满了对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智慧。比如,《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而寻找连续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儒家思想家时时思考的问题。
孔子对古经中所蕴含的“时”的智慧做了富有洞察力的阐释。《周易》记载孔子解答弟子对于爻辞的疑问,其中几次提及“时”。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见龙在田,时舍(舒)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所有这些,其核心观念就是“与时偕行”。“时”关涉天人关系,也贯通古今关系,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方面,儒家强调永恒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中的变革性。正所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与“简易”。《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这种“变易”并不是一种无序的变化,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成,其中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不论天时,还是人类社会之“时”,都不会停滞,“变”就是必然。因此,儒家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的变革创新精神。
刘飞: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和韧性,而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命力和韧性,在根本上只能来自于其与时俱进、顺势应时的创新创造性。
文化似水,唯有不断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才能不废江河万古奔流、生机无限;反之,没有了新的源头活水注入,再浩荡的江河湖海也会丧失活力,以至于干涸中断和消亡。文化创造力是生命力的彰显,失去创造力生命力就会枯竭;创新性是连续性的保障,开放包容又是创新创造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建基于一种运动发展变化的“生生”宇宙观、世界观和哲学思维。在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看来,宇宙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一往无前、永不停歇的大化流行过程,天地之间、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流动和更新,“变化无穷焉”;生生不已的变化变易之道就是支配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宇宙精神、宇宙之道,也即是天道。由于“生生”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亡,所以“生生”的宇宙根本之道就决定了革故鼎新、去故取新、破旧立新、新事物的产生是世间最好的事情,生成和创新就成为了宇宙天地间的“大善”“大德”。进而,人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禀赋了宇宙根本精神、天地乾坤的精华且最具灵性的存在,是万物之灵长,也就应当要效法天地之道“唯变所适”,不断适应变化、与时偕行、积极进取、刚健有为、日新不已,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日新”“自强不息”就此被确立为中华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和人生价值导向。
2
中华文明讲究和追求的创新是在坚守大道、正道的基础上去守正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为新而新”,守正才能真正地创新创造
王学斌: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所主张的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其前提与预设是以故为基、汲古向前的,没有传承与积淀,绝不会有开拓的可能;没有无数次面临灾厄时的返回式追问,绝不会有面对前方未知的破局勇气与底气。申言之,五千多载的连续性,恰是文明得以创新创造的最大凭依,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笃信返本开新、融旧于新等理念的缘由所在,更是我们对待自身文明的“辩证法”。
刘飞:中华文明讲究和追求的创新是在坚守大道、正道的基础上去守正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为新而新”,守正才能真正地创新创造。达权知变、推陈出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让天地人间的大道、正道、常道得以在时移世变中始终得以保持、彰显而不至于被歪曲泯灭。
“守正”就是要“中正平和”“允执厥中”,就是要从容中道、“中庸而时中”,不偏执、不激越,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守正”同时也意味着创造中要有坚守、坚持和延续。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是说,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不是“乱变”,而是要“归正”“守正”,回到自己所应有的位置、回归自己的本性本分,以充分地实现自身、成就自身;同时,宇宙的变化运动在各个事物“归正”“守正”的基础上达致整体的完满和谐统一——“太和”。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当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是否“十世可知也”时,孔子的回答是“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袭损益,以至于此后百世的礼制皆可推知,人们设定礼法制度其背后所蕴涵的精神和目的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通过礼法来规范人的行为,使得社会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协调配合、“和而不同”的“太和”局面。
守正创新的“守正”就是要“顺天应人”,就是要坚守并顺应大道和天下人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华文明充溢着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理性。传统文化中的大道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道、为民安民守民之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有好生之德”,道的根本要求和规定就是要让天下所有事物尤其是天下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万变不离其宗,都能够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各守本分,都得到充分的滋养、发展和成就。
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名臣管仲曾告诫齐桓公,王者要“贵天”,他明确指出“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既然百姓就是天,那百姓的需求当然要尽全力保障,所以宋代大儒程颐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朱熹则提出“王道以得民心为本”。这些都表达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精神。
宋立林: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面临大变局,其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旧邦新命”。毫无疑问,“创新”成为近代以来时代的最强音,在今天尤其如此。只消看看各地的城市精神,几乎都有“创新”一词,便可体会。然而,如果一味地倡导创新,而忽视了继承,那么也会弊端丛生、遗患无穷。因为如果切断传统,现代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其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追求变革创新的呼号越来越响亮。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贺麟先生曾经感慨:“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贺麟才由衷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要追求的其实应该是一种传承与发展的平衡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变与常的关系。
3
中华文明因不断的创新而充满活力,前途光明远大
王学斌: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审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既要鲜明拒斥固守家底、不思变迁的保守态度,又要警惕不顾传统、推倒重来的“为新而新”。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不忘本来中主动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中华民族所走出的虽繁难不已但终向阳而生的文明之路。
宋立林:时移世易,当我们随着民族解放、经济腾飞逐渐恢复民族自信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更加理性、客观地理解传统文化,也能够以“温情与敬意”礼敬传统文化。但是,礼敬传统,并不是守旧和复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辩证观念。这突出体现在中国文化处理“变与常”的智慧之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是那些能够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核心思想理念,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比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都是历久而弥新,亘古而常新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理应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传承发展好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刘飞: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创新乃是文化的本质和力量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正是源于这种日新不已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禀赋,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弦歌永续,虽百折而不挠,历经风雨沧桑艰难险阻,却总能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今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
中华文明因不断的创新而充满活力,前途光明远大。今天,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久弥新、古老而又年轻、充满无限生机活力的民族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要沿着自己的文明发展逻辑去建设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还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人担当”,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达到新的发展境界去探索开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又是同一个事物、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今中国已从传统走入了现代,我们需要秉持创新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正心诚意,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看待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更需要在文化建设中锐意进取,着力增益现代的文明要素,大力培育人们现代的文明观念和文明意识,建立现代的文明秩序。在继承弘扬和创新创造中书写中华现代文明新华章,这既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又是我们必须要担负起的“文化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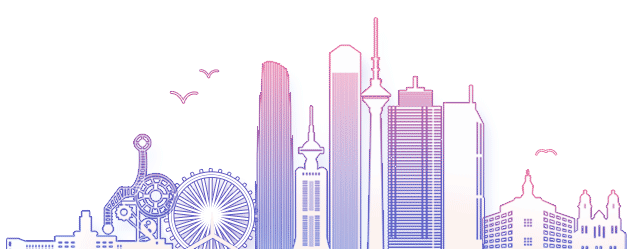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