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存才
唢呐演奏家,河北赵氏唢呐第七代传人,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独奏演员兼唢呐声部首席。1983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代表作《黄土情》《全家福》等。

舞台上的赵存才
印 象
丰富的民间音乐给了他艺术滋养
有一种乐器,可以“朝堂演兴衰,乌巷奏喜丧”,这就是中国民族器乐大家庭中极具特色的唢呐。在民乐演奏中唢呐能起到“桥梁”作用,也是中国民乐的标志性声音之一。天津歌舞剧院唢呐演奏名家赵存才是河北赵氏唢呐第七代传人,他3岁学唢呐,9岁登台演奏,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不久前,他参加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人》节目录制,现场讲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赵存才幼年时随父亲赵占元学唢呐,1979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担任独奏演员。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有三位元老级艺术家──笛子演奏家刘管乐、笙演奏家阎海登、唢呐演奏家殷二文,当年在中国音乐界大名鼎鼎。在老艺术家的指导下,赵存才与笛子演奏家徐佩武、笙演奏家高久林一起成长为民族乐团的中生代名家。
丰富的民间音乐给了赵存才艺术滋养,陕西、河南、云南……凡是有唢呐艺术生存土壤的地方,他都能轻松吹奏出当地小调。他的演奏或深邃古朴,或柔美圆润,或韵味绵长,或高亢悠扬,观众总能听得如醉如痴。他也从不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创新,将唢呐演奏艺术推向新高度,结出硕果。
《全家福》是以安阳地区民间戏曲唱腔、板式、曲牌组合起来的吹奏乐曲,旋律古朴、洒脱、强劲,是赵存才的代表作之一,他对这首乐曲的内涵也有着独到的艺术见解和较为完美的诠释。2005年,他作为天津市唯一入选的音乐家,和其他城市几位音乐家一起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演奏这首乐曲时,他采用循环换气的演奏技法,一口气长时间不留痕迹且保持音色不变。惯于欣赏西洋管乐的奥地利观众惊叹不已,金色大厅里响起了阵阵掌声。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赵存才仍然曲不离口。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让他尽享天伦之乐,孩子对唢呐的天赋和喜爱更让他感到赵氏唢呐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人赓续传承民族音乐,国风雅韵也将在下一代人心中变得更加绚丽缤纷。
唢呐世家第七代传人 少年时考入河北省艺校
记者:您出生在一个唢呐世家,从3岁就开始学唢呐,您是第几代传人?
赵存才:到我这是第七代。我的老家在河北省邢台县,现在当地的图书馆还保存着关于我们赵家唢呐家史的记载。我爷爷过世比较早,我父亲赵占元接班时才8岁,就已经挑大梁了,方圆百里首屈一指。
记者:能一直传了七代人,说明过去唢呐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
赵存才:邢台县以前是直隶省顺德府。听我父亲讲过,当地有一种风俗,假如说两家同时办喜事,轿子走到十字路口,一个往东去,一个往西去,错不开,怎么办呢?按规矩就得两家的唢呐手对着吹,人气差一点儿的就得给对方让路。那个场面就是,大八仙桌子往那儿一摆,唢呐手上桌子,吹起来看啊!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我父亲一吹起来,人们一下子就围过来了,对方那边就没什么人了!我父亲跟主家说,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也不合适。我父亲做人厚道,在同行里边口碑特别好。有一回办白事,主家的儿子据说是个白眼狼,特别不孝,连哭都不哭!我父亲吹了一曲《哭破天》,愣是给这个不孝子吹哭了!观众说:“这师傅太棒了!能把这个不孝子吹哭了,这是高手!”无论什么场合、什么环境,都能用唢呐乐曲来表现。所以说唢呐是非常有魅力的乐器,我特别挚爱唢呐。
记者:您小时候学唢呐,是出于自觉自愿,还是家长强迫您学?
赵存才: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当地成立了一个文艺班。文化馆的人知道我们家是干这行的,就把我招到了文艺班。一年以后我考入河北省艺校,但是学校没有专门教唢呐的老师,请来河北省歌舞团的唢呐演奏家梁培印老师代课。梁老师跟我父亲是发小儿,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管教得特别严。
记者:严到什么程度呢?
赵存才:我那时也就是十三四岁吧,练习时精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梁老师拿一把大戒尺,“啪”一下打到我后背上,瞬间起个大檩子。他说:“往哪儿看呢?你干什么了!”接着拿一个摁钉往树干上一按,说:“两眼不许离开这摁钉,不叫你不许给我停!”那次我一吹就吹了两个小时,不许看别处,不许想别的,只许想音准不准、气息对不对、嘴型对不对。这种严苛的教育让我受益终身,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有时候也拿着一根小棍儿,当然现在不能真打,就是告诉他应该专注。
记者:您觉得天赋和后天的勤学苦练哪个更重要?
赵存才:搞乐器的,不管是哪一种乐器,都需要一定的天赋。所谓天赋,其实首先你要喜爱它,这是必需的。就算练得再好,但你不喜爱这件乐器,天赋再高也是白费。其次是感觉,包括节奏感、音准以及对音乐的敏感性。比方说别人唱一首歌,你听了以后马上能记住,并且能模仿得特别到位,这很重要。
到天津音乐学院深造 不同曲风融会贯通
记者:您是怎么来天津的?
赵存才:我在河北省艺校毕业那年,我父亲过世了。以前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天津音乐学院深造,那是个学东西的地方。”我父亲以前在天津音乐学院代过课,他了解这个学校。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到北京,原址改为河北音乐学院,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当时师资短缺,聘请我父亲去代课。我还留着那张聘书,上面写着“兹聘请赵占元先生为器乐系兼任教师,每月致送兼课钟点费72.5元,聘期自1958年12月1日至1959年1月31日”,下面有缪天瑞老先生,就是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印章。我父亲亲身感受到天津音乐学院的教育氛围,所以嘱咐我有机会去那上学。我从河北省艺校毕业时,天津音乐学院在华北招生,招生老师正好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王玉芳老师,她是拉板胡的。我是带着父亲的热孝去考试的。考完之后,王玉芳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邢台的。她又问邢台有个叫赵占元的你认识吗,我说赵占元是我父亲。王老师就让我下午带一个伴奏的同伴来,要给我录一段音。我是1979年到的天津,缘分结下之后,就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记者:在传承赵氏唢呐的过程中,您是严格继承父辈的演奏方法,还是博采众长,不断吸收其他艺术养分?
赵存才:我从小跟父亲学他的演奏方法,学他对唢呐的挚爱,另外也学民间的一些东西。我进了河北省艺校以后,梁老师教了我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后来我考到天津音乐学院,我的恩师范国忠教授教了我很多不同风格、不同地域、不同色彩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融合在我的演奏中。
记者:您说的不同,是在表现在技巧上还是在曲目风格上?
赵存才:主要是曲目风格不一样,与各地一些戏曲剧种和方言都有关系。
记者:听说您珍藏了一盘录音磁带,听到它总能让您想到父亲?
赵存才:我父亲在我们老家的公社──现在叫乡镇──举办的一些庆功大会上演奏,留下了录音。怎么录的呢?是公社里一个管音响的人,他不知道从哪借了一台录音机,给录了下来,后来送给我做纪念。那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录音,太珍贵了,都是我从小就一直听的。说心里话,现在我都不敢听,一听到那个声音,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些往事,都展现在我眼前了,感情上受不了!
唢呐能让人欢欣鼓舞 也能吹得人耳热心酸
记者:小时候看电视剧《武松》,主题曲就是一首唢呐乐曲,与剧中人物的情感、经历融为一体,听后余音绕梁,唢呐的魅力就在于此吧。
赵存才:对,那是一首山东的民间乐曲,叫《一枝花》。唢呐的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会、秧歌会、鼓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唢呐没有音高,全凭吹奏者的耳音、感觉来控制音调和音准的强弱。这个乐器的张力特别强,既能吹出那种特别喜庆的乐曲,比如像《喜迎春》《百鸟朝凤》,听了让人欢欣鼓舞,又能吹得人内心酸楚,听着想要掉眼泪,有时即便只有一句曲调,也能把人吹得耳热心酸。正所谓“欢乐时如火如荼,悲凉时如泣如诉”。唢呐的表现力特别丰富,模仿力也强,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声音,模仿各种场景的声音,都能惟妙惟肖。
记者:古人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说最能直接表达感情的终归是人的声音。在您看来,唢呐演奏出的饱满深厚的情感是否能超越人声?
赵存才:无论乐器还是人声,无论演奏者还是演唱者,都要把乐曲融入自己的内心,再通过技巧呈现出来,才能传达出音乐的内涵。音乐很奇妙,它首先要感染演奏者自己,然后才能感染听音乐的人。
记者:作为唢呐演奏家,在舞台上就好像在唱一出独角戏。怎么用音乐引领台下的观众跟着您的旋律走,这可能是最能体现演奏家自身魅力的时刻。
赵存才:器乐独奏需要有乐队伴奏,这是至关重要的。独奏演员与乐队要长期排练、磨合,形成默契,这样的话,他在演奏乐曲时稍微一个小动作,乐队就能心领神会。我演奏的时候,比如我把唢呐稍微落下一点儿,乐队也会马上跟着弱下来;然后我再稍扬,乐队就跟着渐强;到气氛热烈的时候,乐队的表演也可以非常隆重。有了这样的紧密配合,才能把一个好作品表现出来。
记者:这说明咱们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奏水平很高。
赵存才: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有我们天津的地方特色。比如我们去台北演出,就展示了天津特色,整场节目就叫“津津有味”,所有的曲目都是我们老院长精心挑选的,演出效果非常棒。
赵存才自述 唢呐不可一天不练
有两次演出,让我终生难忘。一次是在我去维也纳演出前,有两场预演,定在天津音乐厅。恰在此时,我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回了一趟邢台老家。到家一看,我母亲随时可能“倒头”。我们团长给我打电话商量,问我还能不能回来演出?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你到了外边,一定要以事业为重。”
我忍着伤悲回到天津。其实在演完第一场的凌晨,我母亲就去世了,但我家里人知道我要连演两场,就没告诉我消息。然后我演第二场,家里人大概知道我是几点演的,我刚下场,电话就打过来了。我连夜坐车赶回老家,回去以后待了四五天。那种伤悲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太难过了……
之后回天津,还有一场演出,在塘沽体育馆。我对那场演出唯一的记忆,就是我吹不动了!因为平常我可以坚持两三分钟的循环换气吹奏,嘹亮高亢的唢呐声连绵不绝。这个技法的难度在于要利用口腔的“小动作”偷偷换气,换气的同时,旋律和气息并没有受影响,整个过程天衣无缝、不留痕迹。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长期训练,一天也不能停。回老家那几天,我根本没心思练,没摸唢呐。到演出时觉得不对劲儿,状态很差,心里思念亲人,再加上好几天没休息好,都赶到一块儿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也悟出一个道理──这个唢呐真的是不可一天不练!你要是活跃在舞台上,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内行就知道;三天不练,观众都能听出来!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每天仍然会吹唢呐。平常给学生上课就得做示范,不做示范学生没有这种听觉上的感受,他就找不到这个音色,记不住这个音色。这也是我父亲、老师教我的步骤、方法,我现在一闭眼就能想起我父亲吹的那个音色,他和梁老师、范老师吹的音色都不一样。
还有一次演出,是在山东的胜利油田,只有一名观众。这名观众在海上一个油井工作,他在油井一待就是半个月。油田的领导带着我跟一名吹笙的老师一起去给他演出。完了之后,那名观众都没顾上跟领导打招呼,直接握着我们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能给我带来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内心的那种激动让我也特别感动。我感觉作为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送去更好的作品,这是我们的使命。(陈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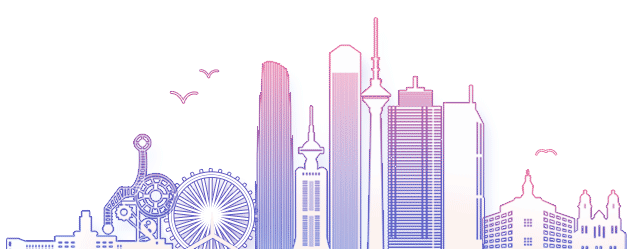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