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
十几年来,每年我都会找时间去蔡美彪先生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办公室或者东总布胡同的家里坐会儿,时间有长有短,有时是有事请教,更多的就只是聊聊天。查看近年的微信记录,2018年初看望蔡先生,91岁的他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我跟他说起今年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0周年,也是中华书局开始专业出版之路60年,蔡先生说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考古发掘、古籍整理和民族调查三个方面,古籍整理就在其中。2019年初看望蔡先生,他将自己的藏书《元典章》法律馆本送给中华书局图书馆,并亲手将这套书从书架上取下交到我手中,说这套书是他1950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时候买的,跟随他近70年。2020年1月21日,我最后一次去看望蔡先生,从早上聊到中午,蔡先生讲了他一贯重视的古籍整理、考古、民族研究,有感于现在的情况,他特别说道:学术研究不同于宣传,学术研究旨在“破解难题,探索未知”!
这一年受疫情影响,我没敢去造访。今年新年后,北京经历了几天极寒天气,走在路上,我突然就想到了蔡先生,一阵揪心。没承想寒潮过后的1月14日,蔡先生却永远地走了。天寒地冻,我又痛失一位引路人。
二十四史驻心田
第一次见到蔡先生的情况,已经无从追忆。2006年4月5日,蔡先生参加了中华书局在香山饭店召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这是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第一次对外征求意见,北京地区著名的文史学者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田余庆、蔡美彪、徐苹芳、白化文、楼宇烈、陈高华、陈祖武、安平秋等诸先生悉数到会,就二十四史修订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论证。未能到会的季羡林先生写来了书面发言《我的建议》。季先生文末的一段话,在我过去十几年工作中,常常响彻耳畔。他说,学术界、出版界也是有黄钟和瓦釜的,我们的责任是,拿出良心,尽上力量,让瓦釜少鸣,或者不鸣,让黄钟尽量地多鸣,大鸣而特鸣。他直言:“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
蔡先生在会上详谈了他所知的二十四史点校情况,最后说:“学者写史学文章都用点校本二十四史,说明点校本是公认的权威。威望很高,责任也很重。错的地方就应该改正,否则对读者有不好的影响,进行修订很有必要。”又说:“有两点建议:第一,广泛征集资料,为修订工作服务。第二,要通过修订工作培养一批人才。”作为前面一段话的补充,蔡先生后来还跟我说,过去30年,不管论文还是专著,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包含着众多点校者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四史点校的成绩和贡献,并不限于古籍整理,更是对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
香山会议之后,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全面展开,而各史当年的点校情况、现在的队伍情况,以及修订工程如何开展等很多问题仍然困扰着我,我亟须听到蔡先生的意见。我电脑里保存了一份与蔡先生谈话的录音,是在香山会议后的5月23日,地点是东厂胡同蔡先生办公室。蔡先生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从不敷衍,即使是涉及对人的评价,也从不模棱两可。蔡先生的看法总是平实公允,即使是否定性的意见,也不觉得他在随口臧否人物。蔡先生看问题非常有思想高度,但又紧贴现实。在谈到修订目标和工作实际时,蔡先生说:
过去我们常引马克思的话,说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要不畏艰难险阻,在崎岖小路上前进。艰苦大概是难免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从实际出发,我们实际能力能做到的。前几天有记者访问我,问我一个很大的题目,说以你的经验,怎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这个题目太大。我说马克思主义是很大的思想体系,有很多内容,我理解具体运用就两条:一条是从实际出发,一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就是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辩证法。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我们这个工作,有很多事想得都很好,但具体落实的时候还是从实际出发,达到我们实际能够达到的要求。
就是在这一次请教之后,我们逐渐明确了修订工作的一些总原则,包括最大限度继承点校本成绩,弥补完善点校本缺憾,形成一个新的升级版本。特别是复校底本的工作,因为大多数点校本的工作底本未能保留下来,加之“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体例,使得我们并不清楚点校本与底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因此蔡先生说,底本复校工作,哪怕校出来没有差异,也是成绩,我们知道了点校本与底本完全一致,这就是成绩。蔡先生非常形象地说:“0是重要的数字,0也是成绩。”由此蔡先生还说,修订不能求多,对点校本的修订不能以校改多少论成绩。受蔡先生的启发,我归纳出了“程序保证质量,一切可回溯”的工作要求,推行至今。
2007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召开。蔡先生在会上风趣地说:“刚才发言的都是各级领导,我是布衣之士,只能讲两点杂感。一点是缅怀旧往,再一点是展望未来。”蔡先生再一次强调点校工作的学术价值:
过去唐长孺先生说过,一条校勘记就像一篇硕士论文。这话讲得很深刻。校勘就考验你对底本的比较判断,标点就标志着你对史料的理解。判断和理解写成文章就是论文。校勘一个字也可以写一篇考据文章。但我想其价值恐怕不仅仅相当于一篇论文,而是从作用上甚至可以说超过一篇论文。因为你写一篇论文,一篇考据文章,可能没几个人看,越专门越窄,不见得能发挥多大作用。但是如果你把考据校勘的结果表现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上,通过校点展示出来,读者用的可就多了,作用就更加广泛。过去胡适说,发现一个字相当于发现一颗恒星,这当然有所夸大,但是说写一条好的校勘记,相当于或者大于一篇考据文章的作用,我认为并不为过。
最后蔡先生说到了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难与易:
这个工作真正做起来难度不小,因为前人已经做了,而且很有成效,已经通行30年,被学术界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做,有容易的方面,有难的方面。从难的方面讲,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一步,虽然是一步,不见得比原来的容易。我想到刘翔百米赛跑,得了冠军,每次记录之间差距还不到一秒,零点零几秒,这零点零几秒的难度比起跑时候零点零几秒的难度要大得多。水平就表现在这儿,能否得金牌就看这儿。
后来应我们的请求,蔡先生担任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审定委员,并先后亲自主持了辽、金、元三史的修订方案审定,还陆续参与审读了辽、金、元三史的样稿。特别是《辽史》定稿前,主持人刘浦江教授已经病重,特别期待能看到老先生的外审意见。蔡先生没有丝毫耽搁,让刘浦江生前看到了他的审稿意见。档案还保存了蔡先生提交的《辽史点校样稿读后随记》,一篇2000字短文,能够看到蔡先生的高度评价和认真严格的审查。蔡先生说:
《辽史》修订点校样稿五卷收阅,此项工作启动未久就有这样的成果,令人敬佩。粗读一过,深感点校组工作仔细认真,思考周密。点校者对有关史料研究有素,博引旁征,得心应手。照这样下去,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企予望之。
接着他条列了标点和校勘存在问题十例,并再三叮嘱:
点校工作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用力多而见效少。《辽史》材料少而错误多,难度更大。因而需要反复推敲……校书如秋风落叶,难得尽扫,但改动原书,务须谨慎,请多留意。
蔡先生对修订工作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在收到新的修订本之后,他都会给我提出具体意见或者需留意的倾向。《史记》修订本印出征求意见本,蔡先生给我打电话,指出修订缘起中的一个用词不妥,原文是“……进行调研,确定了承担单位和主持人”,蔡先生说:我改了一下,“确定”不好,改用“选聘”。不能把主持人当作你的下级,你去选定了谁就是谁,这不行,人家是来支持咱们工作的,是聘请人家来。这件小事给了我长久的教益,也可见蔡先生的为人风范。
古籍整理常牢记
蔡先生对中华书局有特别之情,首先是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所参与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缘故,再就是与中华书局老一代领导人金灿然先生的深厚情谊。
1997年年底,蔡先生在《书品》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回顾了他亲历的1958年9月13日“标点前四史及重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并首次公布了由他起草的会议纪要,以及其后报送毛主席批示的全过程。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序幕是如何拉开的,终于不再是谜。
2008年前后,我看到联经版《顾颉刚日记》中关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的记录有多处提到蔡先生,于是我把日记做了摘编,送去给蔡先生供他回忆参考,请他写一篇《资治通鉴》标点情况,这就是发表在《书品》2008年第3期上的《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
《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是用新的方式方法整理出版古代典籍的最早尝试,不但奠定了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学,也引领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方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蔡先生从1950年代起就在范文澜先生身边工作,亲历了新的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古籍小组的创建,亲历了科学院史学三所的分设和《历史研究》的创刊,亲历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组织实施……
在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开幕前,蔡先生看了会场外陈列的二十四史点校档案展,非常激动。他说:
看到过去的档案和照片,我感慨特别深。外边档案展览的第一件就是我提供的——吴晗起草的、以范老和吴晗名义写给毛主席的关于标点二十四史的报告。当时开这个会,传达主席指示之后,范老召集几个历史所的同志研究,要我做记录。我把记录整理之后,送给吴晗,他修改了两句,然后送给主席,还附了一封信。后来接到主席回信,明确了任务。会上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一些,范老怎么发言,吴晗怎么发言,我都还记得。但是现在参加这个会的,只剩下我这个做记录的人了,都不在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汪篯先生与中华版《唐六典》的小文,里面引到汪篯到公安医院看望金灿然,给金灿然的留言纸条。蔡先生看后特地打电话补充他所知道的情况,金灿然在公安医院去世时,就是蔡先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参与治丧的。蔡先生后来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每天上下班往返于总布胡同、东厂胡同,都要经过王府井大街36号。他说:“中华书局现在在王府井的读者服务部,起的名字叫灿然书屋,我几乎每天上班都看到这四个大字,深感慰藉。灿然书屋四个字,就说明他的贡献并没有被后人忘记,大家还在怀念他。”
天假余年多成果
在我与蔡先生交往的前半段时间,他一直每天到所上班,主要工作是完成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他自己的著作再版一直没提到日程。我曾经一再提出为蔡先生出文集,先生总是回答我说“只要还能写,就不去编”。2012年前后,蔡先生终于先后交给我们《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和《成吉思汗小传》三部书稿,后来又将《史林札记》编好交付我们。
《辽金元史考索》出版后,我们邀请京津地区的辽金元史学者齐聚中华书局,老中青三代学者高度评价了蔡先生的为学与为人。蔡先生最后发言,说得特别风趣:
中华通知我开这次会,是对我的书做评论,我说我就不出席了,因为我一出席,大家就照顾面子,不好批评了。我不出席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后来推辞不了,还是出席一下,可以接受大家的当面批评。不过我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呢,好像批评很少,鼓励过多,我有点不安了。因为有些可以说是过奖了,奖誉过甚。我也不说我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绩,都没有成绩就不该出版了。但大家把优点讲得过多了,超过我的实际。
他开玩笑说:现在街上有好多老店要歇业,要做清仓甩卖,两块钱一件儿随便挑。我出这两本书,都是几十年前写的,对我来说是“清仓甩卖”,对中华书局来说是“废品回收”。蔡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最让我感动,他说:
为了答谢大家的鼓励,我也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现在我还可以勉强做点工作。司马光《通鉴》写完给神宗上表汇报:“目视昏近,齿牙无几”,“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其实他当时才六十几岁。马克思活了65,范文澜活了75,我现在能活85,应该是天假余年,希望继续在大家的支持、帮助下,我一定好好做点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成吉思汗小传》是1962年蔡先生与金灿然同去内蒙古参加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年学术讨论会时,金灿然跟蔡先生的约稿。蔡先生在《前言》里交代了缘由:
我接受了他的邀约,即着手写作。不幸的是,两年后初稿写成,他已患严重的脑病,不能看稿。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他便在动乱年代凄凉逝去。我把书稿放在柜子里,也不再去理它,不觉已过了50年……现在拿出来出版,奉献给读者,也算向灿然同志交了卷。可惜已不能再送他看看,不知是否合他的意。
纸短情长,寄托了蔡先生深深的怀念。
借蔡先生《成吉思汗小传》和此前乌兰老师《元朝秘史(校勘本)》出版的机会,我们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了“元代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座谈会”,并庆贺蔡先生米寿。蔡先生在会上谈元史典籍整理时说:
《史集》《世界征服史》,从洪钧、屠寄到翁独健、何高济,经历了80年;《元典章》,从沈家本到陈垣、陈高华,经历了100年;《元朝秘史》,从叶德辉到乌兰,经历了100年。可见古籍整理不是一时之事,后来的成果都包含了前人的贡献,但关键要看你比前人有多少进步。
蔡先生这一席话,切中古籍整理长期性的特点,也饱含期待。
近几年去看望蔡先生,总能了解他近期的工作动态,接收他陆续出版的新书。每次聊天,从社会新闻、学术动态、掌故逸闻,一直谈到中华书局,满满的都是温暖的鼓励和豁然的启迪。(徐俊)
- 上一篇:王继才:一家三代守护同一面旗帜
- 下一篇: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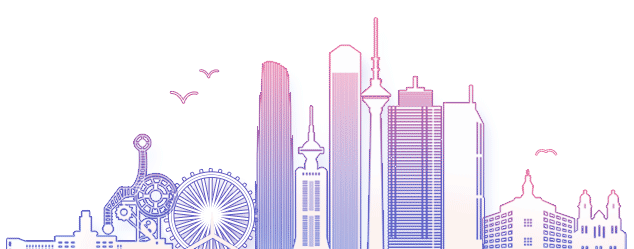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302000985号